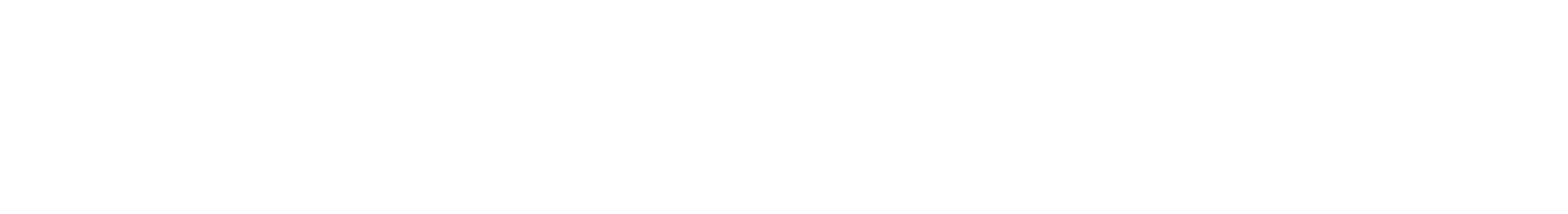来源网络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船舶具有拟人智化特性,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深深影响了以船长及船员为规制对象建立的国际海事公约体系。智能化是船舶驾驶技术发展的趋势,国际海事公约以纳入和转化的方式融入我国国内法规则体系,二者在规则设计上具有相洽性。在法律层面因应船舶智能化发展方向,不仅需要关注相关国际规则变革,也需要考虑智能船舶领域的法律需求,从立法机制层面适应船舶智能化的新业态。
人工智能船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海事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发展智能船舶已经成为国际航运界的共识。2017年12月,全球第一艘万吨级智能船舶通过伦敦船级社认证,正式交付使用。同年,挪威、日本等国宣布在2019年推出用于国际航行的无人驾驶船舶。美国等国家已联合向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IMO)提交人工智能船舶立法范围的方案,国际海事委员会也已设立国际公约与人工智能船舶国际工作组,起草相关行为准则。我国商船船队规模排名世界第三,人工智能船舶研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船级社发布全球首部《智能船舶规范》,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目标。2018年12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我国智能船舶发展顶层规划提出具体方案。可见,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船舶时代已经到来。
船舶智能化是航运技术与外部智能技术的融合。智能船舶的发展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综合船桥系统应用于船舶自动化驾驶至今,远程测控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成果不断融入船舶驾驶技术,不同组织或团队相继公布了各自的智能船舶研发路线。英国劳氏船级社着重分析人与船舶的关系,侧重于网络支持方案。挪威船级社关注机载智能设备操作可用性,关注智能系统带来的潜在风险。韩国现代重工推出综合智能船舶解决方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提高船舶运营智能化水平。国际海事组织侧重智能船舶技术路线图,关注智能系统在不同阶段的实现形式。殊途同归,上述船舶智能技术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利用新技术改进船舶自主控制功能,在兼顾航行安全及运营效率优化前提下,通过不断的技术融合提升船舶数字化水平。
船舶立法在我国属于海事立法范畴。国内海事立法对国际海事公约相关内容作了纳入或转化,形成了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相接洽的立法模式。因应船舶智能化时代变革,国内海事立法应立足于人工智能船舶发展新业态,参照相关国际公约发展趋势,在为主管机关执行监管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的同时,逐步将人工智能船舶规制纳入法治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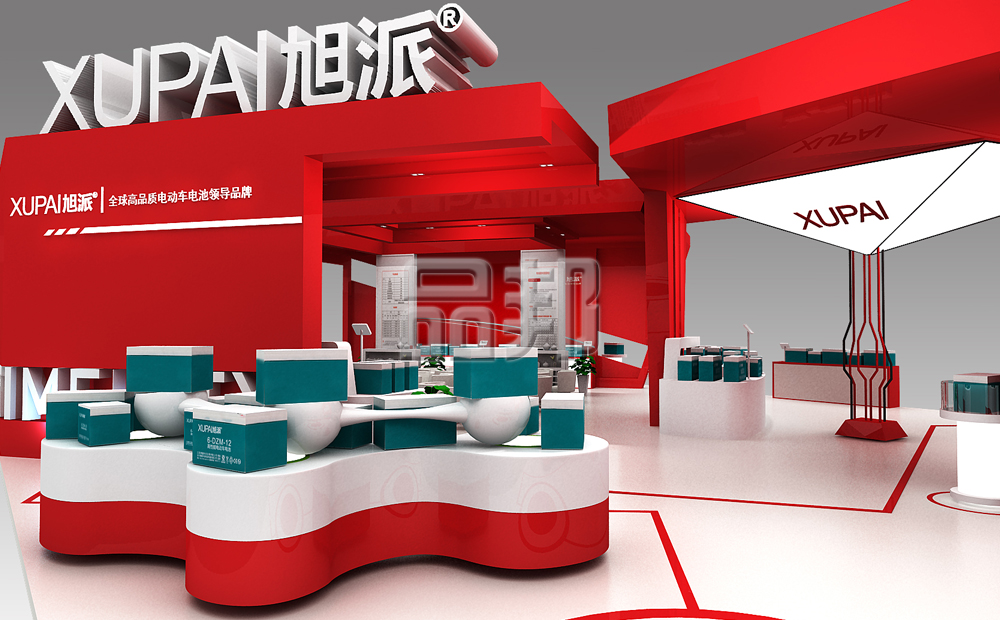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船舶的属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船舶具有拟人化特性,突破了船长及船员对船舶航行的绝对控制。如何认定人工智能船舶的法律属性,关乎相应海上航行规则的适用及法律责任的认定。对此,国内法需要明确人工智能船舶属于“船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船舶本质上依然是用于海上航行的可移动设备,服务于载人、载货或其他交通运输目的。人工智能船舶是否享有独立法律人格,不仅在于其人智化的社会属性,更需要考虑人格拟制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弥合度。具备独立财产是法律拟制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从法益平衡出发,赋予人工智能船舶有限的法律人格,必然需要发挥财产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否则就不可能模仿法人制度,对智能船舶设定独立的责任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
二是采取技术控制与法律控制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机制。技术控制以风险预防为基本理念,设定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过程的责任制度,法律控制应侧重于对人工智能船舶的研发、使用和管理建立限制机制、禁止机制以及惩戒机制。技术规则法律化,是海事立法的特色及惯用方式,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海事立法中的适航义务、避碰规则、停靠规则等规定,无一不是发端于技术规则,最后被立法吸纳,演变成法律规则。国内立法在规范智能船舶时,尤其应当适时吸收中、外船级社制定的智能船舶技术标准,将比较成熟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法律规则。
三是将岸基远程控制者纳入法律责任体系。在船上配置船长、船员,不是智能船舶营运的必要条件,智能船舶的出现将挑战现有法律中有关适航义务的规定。人工智能船舶进入海上运营已成定局,但短期内并不会取代传统船舶。智能船舶出现后,船长履行的适航保证义务,将由岸上控制人员代为履行。岸基远程控制者不等同于船长、船员,但基于其控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需要将其纳入规制人工智能船舶海上航行法律责任体系,承担相应的替代或补充责任。
四是对智能船舶海难救助义务作出减免性规定。《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5章第33条、《海洋法公约》第98条及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均规定,船长及船员应当履行救助的义务,尽力救助遇险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事故现场或者逃逸。部分人工智能船舶由于其自身结构特点,或者因船舶属性及救生设备的配备状况,决定智能船舶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救援条件。海难救助义务的本质是互助义务,无人驾驶船舶因为不存在船上控制人员而降低了自身救助需求,从法益衡量出发,立法应减轻或免除岸基远程控制者的救助义务,或者制定替代性解决方案,规定岸基远程控制者应当履行通知义务,将海上人员遇险的信息转移至其他具备救助能力的船舶或救助中心。藉此,对智能船舶控制者的海难救助法律义务做出相应减免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船舶具有拟人智化特性,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深深影响了以船长及船员为规制对象建立的国际海事公约体系。智能化是船舶驾驶技术发展的趋势,国际海事公约以纳入和转化的方式融入我国国内法规则体系,二者在规则设计上具有相洽性。在法律层面因应船舶智能化发展方向,不仅需要关注相关国际规则变革,也需要考虑智能船舶领域的法律需求,从立法机制层面适应船舶智能化的新业态。
人工智能船舶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海事领域的重要应用成果,发展智能船舶已经成为国际航运界的共识。2017年12月,全球第一艘万吨级智能船舶通过伦敦船级社认证,正式交付使用。同年,挪威、日本等国宣布在2019年推出用于国际航行的无人驾驶船舶。美国等国家已联合向国际海事组织(以下简称IMO)提交人工智能船舶立法范围的方案,国际海事委员会也已设立国际公约与人工智能船舶国际工作组,起草相关行为准则。我国商船船队规模排名世界第三,人工智能船舶研发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中国船级社发布全球首部《智能船舶规范》,2017年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目标。2018年12月工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智能船舶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1年)》,对我国智能船舶发展顶层规划提出具体方案。可见,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船舶时代已经到来。
船舶智能化是航运技术与外部智能技术的融合。智能船舶的发展经历了从局部到整体的渐进式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综合船桥系统应用于船舶自动化驾驶至今,远程测控技术、互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等科技成果不断融入船舶驾驶技术,不同组织或团队相继公布了各自的智能船舶研发路线。英国劳氏船级社着重分析人与船舶的关系,侧重于网络支持方案。挪威船级社关注机载智能设备操作可用性,关注智能系统带来的潜在风险。韩国现代重工推出综合智能船舶解决方案,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提高船舶运营智能化水平。国际海事组织侧重智能船舶技术路线图,关注智能系统在不同阶段的实现形式。殊途同归,上述船舶智能技术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利用新技术改进船舶自主控制功能,在兼顾航行安全及运营效率优化前提下,通过不断的技术融合提升船舶数字化水平。
船舶立法在我国属于海事立法范畴。国内海事立法对国际海事公约相关内容作了纳入或转化,形成了国内立法与国际公约相接洽的立法模式。因应船舶智能化时代变革,国内海事立法应立足于人工智能船舶发展新业态,参照相关国际公约发展趋势,在为主管机关执行监管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的同时,逐步将人工智能船舶规制纳入法治轨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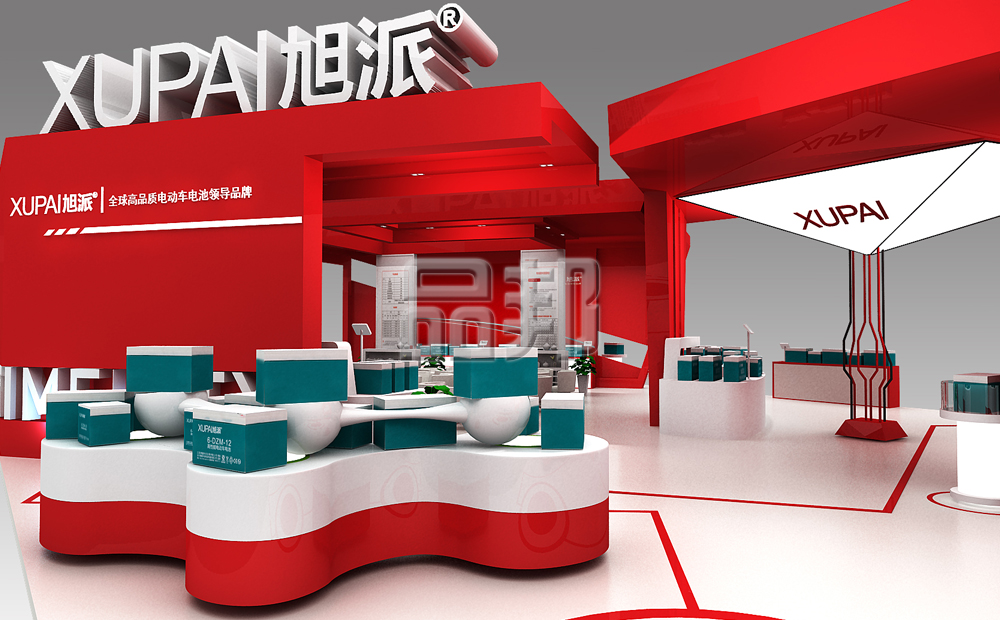
一是明确人工智能船舶的属性。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得船舶具有拟人化特性,突破了船长及船员对船舶航行的绝对控制。如何认定人工智能船舶的法律属性,关乎相应海上航行规则的适用及法律责任的认定。对此,国内法需要明确人工智能船舶属于“船舶”,原因在于人工智能船舶本质上依然是用于海上航行的可移动设备,服务于载人、载货或其他交通运输目的。人工智能船舶是否享有独立法律人格,不仅在于其人智化的社会属性,更需要考虑人格拟制与法律责任之间的弥合度。具备独立财产是法律拟制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从法益平衡出发,赋予人工智能船舶有限的法律人格,必然需要发挥财产制度的基础性作用,否则就不可能模仿法人制度,对智能船舶设定独立的责任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
二是采取技术控制与法律控制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机制。技术控制以风险预防为基本理念,设定从技术研发到应用过程的责任制度,法律控制应侧重于对人工智能船舶的研发、使用和管理建立限制机制、禁止机制以及惩戒机制。技术规则法律化,是海事立法的特色及惯用方式,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海事立法中的适航义务、避碰规则、停靠规则等规定,无一不是发端于技术规则,最后被立法吸纳,演变成法律规则。国内立法在规范智能船舶时,尤其应当适时吸收中、外船级社制定的智能船舶技术标准,将比较成熟的技术标准转化为法律规则。
三是将岸基远程控制者纳入法律责任体系。在船上配置船长、船员,不是智能船舶营运的必要条件,智能船舶的出现将挑战现有法律中有关适航义务的规定。人工智能船舶进入海上运营已成定局,但短期内并不会取代传统船舶。智能船舶出现后,船长履行的适航保证义务,将由岸上控制人员代为履行。岸基远程控制者不等同于船长、船员,但基于其控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需要将其纳入规制人工智能船舶海上航行法律责任体系,承担相应的替代或补充责任。
四是对智能船舶海难救助义务作出减免性规定。《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5章第33条、《海洋法公约》第98条及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均规定,船长及船员应当履行救助的义务,尽力救助遇险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事故现场或者逃逸。部分人工智能船舶由于其自身结构特点,或者因船舶属性及救生设备的配备状况,决定智能船舶本身不具备良好的救援条件。海难救助义务的本质是互助义务,无人驾驶船舶因为不存在船上控制人员而降低了自身救助需求,从法益衡量出发,立法应减轻或免除岸基远程控制者的救助义务,或者制定替代性解决方案,规定岸基远程控制者应当履行通知义务,将海上人员遇险的信息转移至其他具备救助能力的船舶或救助中心。藉此,对智能船舶控制者的海难救助法律义务做出相应减免2019年中国国际海事技术学术会议和展览会。
品邦广告,14年专注营销型展台设计搭建、活动策划、展厅施工,提供系统化、个性化的营销解决方案。40名展台设计人员、展会营销团队,让你在展会上智放光彩!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荐搭建商,展会搭建业务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诺基亚、费列罗、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伴,精致设计、未来科技,全案策划。我们交付给您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展台。闫小姐:微信同号13918355988。在线咨询